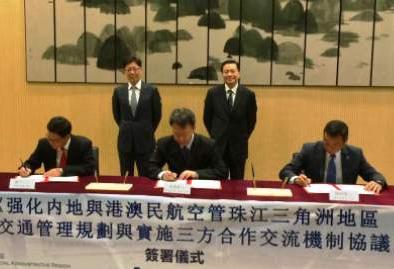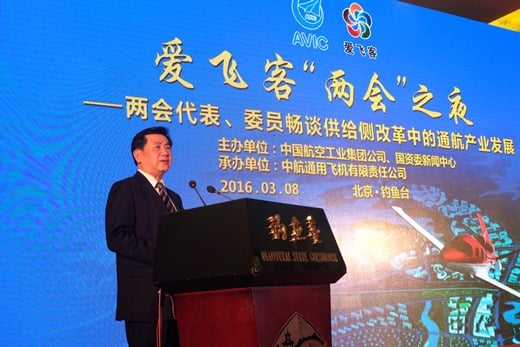毛剛:沒有想象,則無法超越
從小就懷揣著工程師的夢想,毛剛沒有按照父親的規劃成為一名老師,而是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叩開了夢想的大門。從民航科研實驗室里埋頭苦干的工程師,到精通市場營銷的總經理,他見證了民航二所從“吃皇糧”走上“找飯碗”的市場化之路,也親歷了民航科研事業發展的“中國速度”。
從業30年,他與自動行李處理系統結伴同行20載。他和他的團隊專注于此,從追趕者變成行業的引領者。他說,這一輩子,干好這一件事,他就心滿意足了。
毛剛的父親是一名老師,姐姐和弟弟也是老師。按照父親的規劃,他本應在四川瀘州的某個小鎮上教書育人。初中畢業時,出于對工程師的憧憬,他毅然放棄報考瀘州師范學校,選擇了離家50公里的一所高中。兩年后,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工程專業,叩開了夢想的大門。
1988年7月,毛剛進入民航二所工作。在隨后的30多年里,從民航科研實驗室里埋頭苦干的工程師,到精通市場營銷的總經理,毛剛完成了個人事業的一次次突破,也親歷了民航科研事業發展的“中國速度”。而今,他依然專注于中國自主研發的科研產品,堅持“中國造”,為民航強國建設貢獻智慧與心血。
從小就懷揣著工程師的夢想,毛剛沒有按照父親的規劃當一名老師,而是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工程專業。圖為1986年毛剛(左)和大學同學參觀航空博物館留影。
從業30多年,毛剛與行李自動處理系統結伴同行20年,獲得了無數榮譽。他說:“這20年就像白駒過隙。幸運的是,我和我的團隊抓住機會,專注于這件事,從追趕者變成行業的引領者。未來,我們還將推動項目向智能化方向發展。這一輩子,干好這一件事,我就心滿意足了。”
工程師的市場“經”
1989年,毛剛參與重慶江北國際機場辦理乘機手續電腦電視顯示系統建設項目。這是他工作后參與的第一個機場弱電項目,這個項目拉開了民航二所自主研發產品逐步走向市場的序幕。圖為毛剛(左一)和老同志在完成第一個機場弱電項目后留影。
大學畢業時,毛剛在眾多軍工企業和民航二所中選擇了后者,正式結緣民航。在他的記憶中,位于新津的民航二所占地十余畝,其間分布著一棟三層辦公樓、一個生產車間、兩棟家屬樓和一棟單身宿舍樓。第一眼看到這些,毛剛很失落。他說:“這與我想象中民航的‘高大上’相比,差距實在太大了。”然而,隨著對行業了解的深入,他意識到,民航是一個與國際接軌的行業,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民航一定會迎來巨大的發展。
那個時候,民航二所屬于事業單位,吃的是“皇糧”,靠事業經費發工資。隨著改革浪潮來襲,在民航局逐步縮減事業經費下撥的壓力下,民航二所踏上了從“吃皇糧”到“找飯碗”的市場化之路。很快,民航二所舉全所之力研發的亞運會記分牌亮相北京亞運會,成為其走上市場化道路的標志性事件。參與其中,毛剛第一次感受到工程師不僅要懂技術,更要懂市場。
1993年,在遷回成都的第4個年頭,民航二所市場化改革啟幕。一方面,進行干部管理體制改革,建立起權力與責任對等、責任與待遇掛鉤的競爭聘任制度;另一方面,進行經營管理體制改革,將原來的研究室運營整合成專業公司經營。隨后,民航二所的公司如雨后春筍般成立,并迅速在市場競爭中組合、重生。這段看似混亂的歲月,讓民航二所和二所人親歷了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為后來直面市場奠定了基礎。
1993年,毛剛第一次赴西藏參加拉薩機場航班顯示系統建設。伴隨著嚴重的高原反應,他堅持完成任務。通過幾年工作的摸爬打滾,他從民航二所老同志那里學到的不僅是技術,更體會并傳承了民航二所科技工作者勤勤懇懇、吃苦耐勞的精神。圖為毛剛在項目即將完工時留影。
在此期間,毛剛逐步走上管理崗位,歷任民航成都電子設備有限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工程部副經理。在民航科研機構待的時間越長,毛剛越能體會民航科研人員的不易。他坦言:“在民航業,一個好的項目從無到有,從雛形到市場推廣,實在太難了。”那種深深的無力感也讓年輕的他動搖過,想過放棄,想過離開。
有一次,他約朋友去外地調研與民航無關的新項目。出發前,他突然接到電話,懷孕的妻子要生產了。他果斷更改行程,趕往醫院。這次巧合讓毛剛失去了一次離開民航、獨自創業的機會。看著襁褓中的兒子,毛剛的心變得格外柔軟,也感到無比滿足。父親的角色讓他多了一份責任,也讓他的內心漸漸成熟起來。待他重新思考事業發展時,離開民航的念頭再也沒有出現過。
那個年代,偏居西南,毛剛出差的機會并不多。幾次去北京,他見識到首都機場行李自動處理系統的快捷、便利。這讓他上了心。在經過多方調研后,他得知首都機場的行李自動處理系統價值2700萬美元。不少人認為,這筆錢存銀行吃利息都足以支付人工費,買自動設備太不值了。從與專業人士的溝通中,毛剛了解到,就連國際行李自動處理系統集成商對中國市場的前景也不大看好。面對各方質疑,毛剛骨子里科研人的質疑精神讓他陷入沉思。他想,中國發展速度快,各大機場如果都用進口設備,不僅產品成本高,后期維護費用也不少。按照這個思路,他大膽暢想,要是民航二所能提供這樣的設備,既能解決其生存問題,也能為行業提供技術支持,那該多好啊!
“奧拓”的逆襲之路
1999年初,一次偶然的機會,毛剛在與民航二所所長交流時談到了行李自動處理系統研究項目。令他驚喜的是,自己的一番話得到了所長的認可,并指示他著手向民航總局報批。進入21世紀,中國民航迎來了高速發展期。民航二所相繼創辦了一批科技產業實體,走上了科工貿一體化的發展道路,大力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其中,行李自動處理系統的自主創新之路,無疑是民航二所堅持“中國造”的最佳范本。
在當年上報計劃的最后一天,行李自動處理系統項目立項申請書被送到了民航總局。傍晚時分,返程的毛剛和所長遇上大堵車,一路走走停停,心里格外焦急。北京回成都的航班一天就幾班,無法改簽。趕不上飛機怎么辦?為了趕時間,出租車一抵達機場,他們就跳下車,一路狂奔。最后,在飛機起飛前幾分鐘成功登機。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毛剛依然感覺緊張、激動、心跳加快。他說:“當時我就預感到,今后行李自動處理系統的研發之路不會一帆風順,而是會經歷很多這樣的緊張時刻,但結果一定不會讓人失望!”
在毛剛的帶領下,行李自動處理系統樣機于2001年通過民航總局鑒定驗收。在民航總局的大力支持下,放大實驗落地貴陽機場。在貴陽機場系統真正上線后,分揀口從樣機時代的2個增加到10多個,測試中時常出現分錯的情況。毛剛和項目組同事通宵達旦反復討論、改寫程序,一個點一個點地查找并解決技術問題。因為熟悉系統,毛剛總是那個提思路、換想法的人。
2001年,行李自動處理系統剛開始在實驗室里進行起步研制和測試時,時任民航局副局長的楊國慶(左一)就非常關注其研發進展,專注地聽取毛剛(右四)匯報階段性研究成果。
2004年,重慶機場項目完成后,在行李系統領域擁有老大哥地位的某國外知名集成商的市場總監打了一個生動的比方:“民航二所的水平就是一輛奧拓,新加坡的英特隆可以算是帕薩特,我們才是真正的奔馳。”言下之意,民航二所實力太弱了。
事實真的如此嗎?毛剛嚴肅地說:“技術水平的確有待提高。技術問題解決不了,我們可以攻關。這是科研人所擅長的。但市場問題解決不了,又不是自己擅長的領域,會更讓人沮喪。作為行業的研發隊伍,有民航局的支持,我們信心滿滿。為早日闖出一條行業科研成果產業化之路,我們必須堅持走下去。”
為占領市場,毛剛的團隊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拿下過幾個項目。為求發展,他們曾與某世界五百強企業談過合作,一度達成共同成立完全對等控制的合資公司的意向,但最終因“限制合資公司只能承接年旅客吞吐量2000萬人次以下機場的業務”被毛剛拒絕。當時,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萬人次的機場只有北京、上海和廣州。毛剛意識到,一方面,中國民航發展快,要是年旅客吞吐量超2000萬人次的機場多起來,未來能做的市場就越來越小;另一方面,一旦成立合資公司,民航二所會失去民航行業的支持,這是一家誕生于民航科研機構的公司不能接受的。
2007年底,在貼錢干活、做著小項目的艱難時刻,毛剛再一次主政,從主抓技術轉為全面管理,挑起了公司發展的重擔。為突破業績瓶頸,在民航二所的支持下,公司以遠低于成本的價格中標青島項目。但是,由于成本太低,工程品質并沒有收到預期效果。
這讓毛剛感到遺憾,更讓他深刻反思。很快,他提出:“沒有品質就沒有生存空間。不能一味地以低價取勝,必須用新的思路和方法解決市場問題,以技術能力、技術水平參與市場競爭。接下來的天津項目采用集中安檢模式,我們必須從這里開始,做好技術突破工作,提升產品品質,為公司的長遠發展打好基礎。”
2010年,毛剛(左二)和民航二所領導及同事一起前往俄羅斯參觀考察,了解國外技術裝備的現狀并尋找市場機會,探討“走出去”的大戰略,隨后幾年民航二所提出了業務轉型的三大戰略,“走出去”取得了豐碩成果。
中國造成就引領者
2011年夏天,距離天津項目二期標書最后裝訂還有兩天,正在海南三亞開會的毛剛接到了一通電話。“你好。我們無法向貴公司供應分揀機,無法提供授權書。”
“為什么?可以給一個理由嗎?”
……
掛掉電話,毛剛撥通了另一家分揀機供應商的電話。當天,他就從海南三亞飛往云南昆明,拿到了分揀機供應授權書。毛剛說:“雖然我們提前一年就簽訂了分揀機供貨意向協議,但在一個多月前,我就覺得對方態度蹊蹺,一直不提供正式授權書。所以,我提前準備了預案,確保項目招標的順利進行。”
問題解決了,但毛剛的心里卻埋下一根刺——沒有核心技術分揀機,被卡脖子的事還會經常發生。掌握核心技術,徹底擺脫國外廠家的制約,勢在必行!此后,毛剛和他的團隊加快解決資金、技術問題,極力推動項目進程。2013年,完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第一版分揀機樣機出爐,并取得民航局許可。
事實上,在取得許可之前,分揀機樣機研發一直處于保密狀態。一次,甘肅蘭州機場建設指揮部指揮長到基地參觀,表達了尋求新技術在蘭州機場進行試點的意愿。陪同參觀的毛剛臨時決定邀請指揮長參觀分揀機測試樣機。得知自主研發的核心技術即將通過驗收,指揮長真誠地表示:“你只要敢到我們機場試用,我就敢用你的東西。支持國產新技術、新產品,我們義不容辭!”這既是對國產設備的認可,更是對毛剛和他的團隊最大的鼓勵。就這樣,分揀機找到了第一個東家。
2017年8月29日,采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托盤分揀機、兼容RFID的行李條碼識別技術、可視化輔助分揀系統、自助行李托運設備、行李再確認等眾多新技術的重慶江北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行李自動處理系統正式投入使用。為確保項目成功,毛剛和項目工程師在現場通宵值守。
十年磨一劍,百煉方成鋼。從貴陽、重慶項目放大實驗,到天津項目集成能力強大,再到蘭州項目和重慶機場3號航站樓使用自主生產的分揀機,民航二所具備了完善的行李自動處理系統技術能力,逐步成為國內外行李自動處理系統的引領者。
面對北京新機場項目,毛剛表示:“經過前期磨煉,我們的技術完備,管理規范,已經不怕任何競爭對手了。然而,我們依然擔心機場建設方對民族工業產品不了解,缺乏信心。”最終,北京新機場給予了這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系統足夠的信任,接納民航二所公平參與競標。在激烈的競爭中,民航二所以完備的技術方案、極具競爭力的價格成功中標北京新機場項目。
經過20多年的努力,行李自動處理系統終于站上了最高舞臺。在許多人眼里,毛剛很難再有像突破北京新機場項目這樣的機會,但對毛剛來說,這已經無足輕重。他的目光早已聚焦到了更前沿的項目研發上。
2018年,毛剛參加中美民航ACP EMDT第13期項目培訓。他通過兩個月的學習與考察,深刻體會到中美民航的管理差異和技術差距。作為民航科技工作者,他更加感覺到建設民航強國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圖為美國聯邦航空局、美國貿發署、ACP項目部負責人為毛剛(右二)頒發結業證書。
自2004年起,毛剛在研發行李自動處理系統時就開始跟蹤、研究射頻識別技術(RFID),以實現行李全程追蹤。經過10多年的潛心磨礪,該技術目前已成功在重慶機場3號航站樓全線投入使用,將行李綜合識別率由之前傳統光學識別的約90%提高到99.7%,并將在北京新機場再次應用。同時,首都機場也已經局部采用這一技術進行測試驗證。隨著包括成都天府新機場在內的更多機場上線RFID,行李全程追蹤有望在全國范圍內真正實現。
毛剛大膽設想:“未來二三十年,機場行李輸送裝置和值機柜臺將消失,行李系統將通過一系列智能技術的運用發生顛覆性改變。”為此,毛剛心里的一粒粒種子——行李目的地編碼小車、高速獨立運載系統、自助引導小車等項目——正經歷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澆灌、培育,等待著結出燦爛果實的那一天。
寄夢藍天
作為一名民航科研工作者,為行業發展助力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希望能從政策層面鼓勵使用自主創新產品。只有有人用了,自主創新產品才能在使用中不斷改進和提高性能。
——毛剛
本期主角
毛剛,現任民航成都電子技術公司副總裁,民航成都物流技術公司董事長。
1988年進入中國民航第二研究所,主要從事技術研發、技術管理及項目推廣應用工作。自1999年起,作為課題組長、項目負責人,負責民航總局重點科研項目“民航機場旅客行李自動分檢系統”課題工作,涉及整個研制、技術攻關、放大試驗、產業化推廣過程。
毛剛負責或參與的研發項目曾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1項、省部級科技獎9項、相關知識產權26項。
責編:admin
免責聲明:
凡本站及其子站注明“國際空港信息網”的稿件,其版權屬于國際空港信息網及其子站所有。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時必須注明:“文章來源:國際空港信息網”。其他均轉載、編譯或摘編自其它媒體,轉載、編譯或摘編的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對其真實性負責。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轉載使用時必須保留本站注明的文章來源。文章內容僅供參考,新聞糾錯 airportsnews@126.com
- 上一篇:民航局副局長王志清調研銀川機場
-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