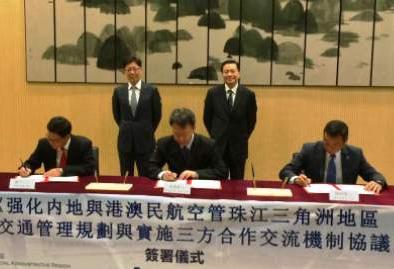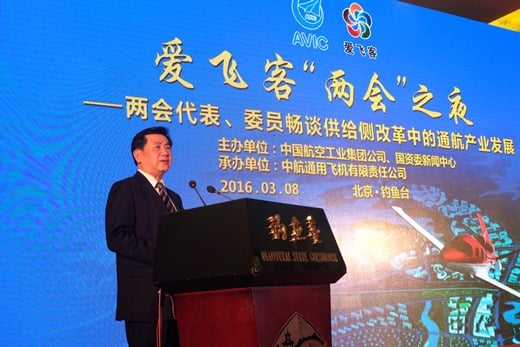陳峰:海航借勢

海航集團(tuán)(以下簡稱海航)董事局主席陳峰的辦公室裝修得頗有古韻,所有中式家具均為小葉紫檀,他告訴《英才》記者:“金融危機(jī)初期,印度小葉紫檀的價格跌到了最低谷,買的時候很便宜,現(xiàn)在這套家具的價值翻了好幾倍。”陳峰說他想“留給后人的是厚重的東西”。
在陳峰辦公桌后面,是一幅抽象的盤龍圖案。“龍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國處世跟西方國家不一樣,他們是船堅炮利的掠奪,中國是一種慈悲的精神。”陳峰如此解釋。
辦公桌對面是一臺等離子彩電,陳峰經(jīng)常坐在紅木椅上開視頻會議,用以遙控全球的運營。
辦公室還有一個小隔間,是陳峰平日清修的地方,屋子雖然不大,但收拾得一塵不染,中式坐榻之上,懸掛著陳峰國學(xué)老師南懷瑾的畫像。
2013年,陳峰六十“花甲”,海航二十“弱冠”。一身黑色中山裝、二目炯炯有神的陳峰,精氣神十足。而海航的成長則更為驚人,20年資產(chǎn)總額已從1000萬元猛增至近3600億元,增長3.6萬倍。“當(dāng)勢到了,誰都擋不住。”陳峰是那種善于度勢之人。
踩準(zhǔn)中國經(jīng)濟(jì)崛起的大勢,陳峰發(fā)展勢頭強勁。從一家地方航空公司,擴(kuò)張為航空、實業(yè)、金融、旅業(yè)、物流五大板塊的大型企業(yè)集團(tuán),成為中國資產(chǎn)規(guī)模最大的航空集團(tuán)。
無論海航怎么變,陳峰雷打不動的是每日用毛筆書寫“禪心隨筆”,現(xiàn)在正重新寫“禪與生命科學(xué)”,每天500字左右。不知道是否可以稱得上書法家。陳峰開玩笑的說自己“不輸古人”,甚至在拍賣會上,他的一幅字曾被一位老者以37萬元的高價收藏,這也讓他小有成就感。
一手實業(yè)、一手資本,一手文化,南懷瑾的弟子,充滿處世智慧,將中國文化與西方管理兼容并蓄,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陳峰和海航,或許會有不同的感觸。
而在資本市場上,有人認(rèn)為陳峰是資本運作的高手,有人在探究陳峰的產(chǎn)融結(jié)合發(fā)展模式,海航旗下共有8家上市公司、20多支基金,擁有租賃、信托、保險、銀行、證券、基金、融資擔(dān)保全金融牌照,龐大的金融資產(chǎn)是怎樣和其實業(yè)相結(jié)合的呢?也有人在好奇,海航近年來如此大手筆的并購,資金從何而來?
風(fēng)動、幡動?還是心動。無論外界褒貶,陳峰灑脫依舊,“我本來就是江湖人士”,又何懼江湖?的確,透過資本擴(kuò)張的表象,又有誰比陳峰更了解真正的資本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當(dāng)初,如果不做到“大到不能倒”,海航很可能已經(jīng)成為別人的一枚棋子。而如今,環(huán)顧四周,面對不利的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關(guān)停230多家旗下公司,刮骨療傷之后,陳峰和海航又靠什么才能繼續(xù)“笑傲江湖”?
抓住所有資本機(jī)會
對于海航來說,資本無疑為其實業(yè)發(fā)展提出了巨大動力。海航的兇猛擴(kuò)張,給外界的印象充滿“饑餓感”。但陳峰卻認(rèn)為海航是“以無我的心態(tài)”來做事,“只問因,不問果,因上努力,果上隨緣。”
然而,海航高速擴(kuò)張之因是什么?創(chuàng)業(yè)者之一的海航集團(tuán)首席執(zhí)行官李先華的看法是,海航自誕生之日,便走了一條與國內(nèi)民航企業(yè)完全不一樣的路,作為中國第一家非國有的航空公司,海航從一開始就與市場、與資本緊密相連。
因為靠海南省融資不現(xiàn)實,靠銀行貸款又沒有抵押,拿到了民航總局頒發(fā)的經(jīng)營許可證之后,海航便開始了第一輪融資。1992年,國家對股份制暫時還沒有明確的指導(dǎo)性文件,當(dāng)時海航便開始嘗試自稱叫“內(nèi)聯(lián)股份制”的融資模式,也就是現(xiàn)在通常所說的私募。
在此后不長時間,國家體改委出臺了《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zé)任公司暫行條例》,允許企業(yè)組建股份公司,在社會上募集資金。于是,海航抓住機(jī)遇,進(jìn)行企業(yè)股份制改造,募集了2.5億元資金,很快于1993年在全國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tǒng)(STAQ)上市。
憑著這筆2.5億元的資金,海航此后又獲得了6億元貸款,購買了兩架飛機(jī)。從此,海航走上了依靠外部融資的金融化發(fā)展道路。
海航的定向募集,使海航獲得了發(fā)展的第一桶金,而此后,基本上每兩年有一次資本運作。
采訪中,一位曾經(jīng)參與過大新華航空定向募資的投資公司董事長告訴《英才》記者:“航空業(yè)和其他運輸業(yè)一樣,在國際上都是依靠金融支撐來進(jìn)行資產(chǎn)的擴(kuò)張,如果沒有資本支持,很難依靠企業(yè)自身積累購買飛機(jī),所以單純對海航資金鏈的質(zhì)疑,其實并不一定科學(xué)。”
但是大規(guī)模的貸款融資可以擴(kuò)大機(jī)隊規(guī)模,同時也帶來了負(fù)債率高企的問題,所以海航在成立之后,非常注意直接融資,來降低資產(chǎn)負(fù)債率。
“高負(fù)債率運營實際上是航空運輸業(yè)的行業(yè)特性,并不是海航的戰(zhàn)略性選擇。相反,海航一直強調(diào)控制負(fù)債率,開展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多元化運營也是為了規(guī)避單一航空產(chǎn)業(yè)的行業(yè)風(fēng)險。事實上,海航的負(fù)債率在資產(chǎn)規(guī)模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始終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李先華說。
陳峰和王健二人曾遠(yuǎn)赴美國,成功說服了索羅斯旗下基金公司參與到海航的融資中。當(dāng)時打動索羅斯公司投資總監(jiān)的并不是陳峰蹩腳的英語,也不是僅有幾架飛機(jī)的機(jī)隊,而是中國蓬勃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和海航市場化的經(jīng)營理念。
索羅斯對海航的第一次投資,可能是其投資史上最小的一筆融資,僅2500萬美元,這并非索羅斯不愿意大手筆投資,而是因為當(dāng)時規(guī)定,在航空運輸業(yè)的中外合資企業(yè)中,外資占股不能超過25%。此后,在海航的融資過程中,索羅斯又第二次參與了海航的增發(fā)。
“索羅斯有一次跟我說,對海航的投資收益率低了點兒,每年只有20%左右,達(dá)不到他們對沖基金的要求,我說沒辦法,誰讓大新華航空要上市,就鬧金融危機(jī)了呢?你趕的時間太不好了。”陳峰對《英才》記者戲說著索羅斯的抱怨:“我告訴他,中國人講信譽也厚道,等以后日子好了,一定考慮你的貢獻(xiàn)。”
與國內(nèi)外資本市場成功對接,為海航的擴(kuò)張?zhí)峁┝速Y金保障,使海航的資產(chǎn)規(guī)模呈現(xiàn)幾何級數(shù)的增長。海航“幾乎抓住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所有機(jī)會,法人股、STAQ系統(tǒng)上市股、A股、B股、外資股、H股,整個兒是中國股票大全!”一位業(yè)內(nèi)人士如此評價。
于是,有人總愛把海航與德隆進(jìn)行類比,但是李先華特別反對這種觀點:“海航和德隆都在做產(chǎn)業(yè)整合,但海航是以實業(yè)為基礎(chǔ),這是海航的初衷,德隆做實業(yè)是手段,目的是資本運作、炒股票、從資本市場掙錢。德隆玩的是虛擬經(jīng)濟(jì),海航是實體經(jīng)濟(jì),這就是海航經(jīng)歷20年風(fēng)雨不倒,但德隆早已灰飛煙滅的本質(zhì)區(qū)別。”
陳峰面對《英才》記者也堅稱:“我從來不做資本市場,一張股票沒買過,一次營業(yè)部沒去過,我是運用資本市場、上市公司的力量來發(fā)展我們的實業(yè),我從來不拿錢來炒股票。”
雖然未經(jīng)證實,但陳峰如所言屬實不炒股票,可能是海航和德隆最為明顯的區(qū)別。
不計代價地做大
比較客觀地說,海航的歷史歷盡艱險。除創(chuàng)業(yè)時險些遭遇的滅頂之災(zāi),還有兩次比較大的危機(jī)。這兩次危機(jī)均出現(xiàn)在1999年上市之后,且都與海航的并購擴(kuò)張相關(guān)。
第一次危機(jī)是在2003年左右,這次危機(jī)與國家產(chǎn)業(yè)政策的調(diào)整有著直接關(guān)系。2000年,民航總局在經(jīng)過充分調(diào)研之后,決定對全行業(yè)進(jìn)行戰(zhàn)略重組,將民航總局直屬的十家航空公司,合并為國航、南航、東航三大航空集團(tuán)。“十并三”極大地改變了整個中國民航業(yè)的格局,三大航空公司建立之后,很多地方性航空公司很可能面臨市場被擠壓,進(jìn)而被三大航空巨頭吞并的危險。對于1999年上市的海航來說,路有兩條,一是選擇壯大自己,不被并購,二是選擇歸附于大航空公司。對于陳峰等人而言,顯然不可能選擇第二條路,白白放棄自己創(chuàng)立的海航。那么,剩下的路只有一條。
2000年重組長安航空,2001年重組新華航空、山西航空,2003年重組西安民生,為了獲得獨立的生存空間,海航不計代價地收購避免了自己被吃掉。
就在海航卯足勁大步前行時,2003年“非典”不期而至,這場災(zāi)難使連續(xù)10年盈利的海航,第一次嘗到了虧損的滋味。
“每架飛機(jī)每月租金40萬美元,飛機(jī)停飛,很多員工沒事做,慘不忍睹!”李先華說。危難時刻,海南省政府拿出15億元,大舉注資海航,幫助海航挺過了“嚴(yán)冬”。
直至2006年,海航再度發(fā)力,重組香港中富航空(現(xiàn)已更名為香港航空)、重組香港快運。2007年,海航收購了比利時Sode、Edipras、Data Wavre酒店,并在同期進(jìn)行了資產(chǎn)結(jié)構(gòu)整理,希望將其麾下的海南航空、新華航空、長安航空、山西航空四家航空公司重組為大新華航空,并計劃2008年在香港上市,以降低資產(chǎn)負(fù)債率。
然而,挑戰(zhàn)還在繼續(xù),接踵而來的金融危機(jī),使民航業(yè)再次受創(chuàng)。“三大航”獲國資委巨額補貼,海航也再次獲得了海南省政府15億元的注資。憑借這有力的援助,憑借之前的未雨綢繆和之后的準(zhǔn)確把握,海航化危為機(jī),度勢成長,再創(chuàng)奇跡。
“中央4萬億投資拉動,銀行催著給你錢,迅速的擴(kuò)張,按照我們的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鏈進(jìn)行發(fā)展。跑馬圈地,一路吃下去,那段太精彩了,都便宜到家了。”陳峰提及那段擴(kuò)張,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2008年之后,海航成立了八大業(yè)務(wù)板塊:航空、旅業(yè)、商業(yè)、物流、實業(yè)、機(jī)場、置業(yè)、酒店。同時利用銀行信貸資金收購兼并,形成了“萬馬奔騰”之勢,同時推出了“超級X計劃”,這一計劃的核心是在第一階段,力爭進(jìn)入世界500強的前100強左右;第二階段,力爭進(jìn)入世界500強的前50強左右。
可以看到的是,海航在2008年的擴(kuò)張比以往更為“激進(jìn)”,2008年下半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機(jī)和歐美債務(wù)危機(jī),導(dǎo)致發(fā)達(dá)國家經(jīng)濟(jì)舉步維艱,被迫進(jìn)行戰(zhàn)略性產(chǎn)業(yè)調(diào)整,這為海航國際并購帶來了難得的機(jī)遇。”陳峰說。比如投資2700萬美元收購?fù)炼銩CT貨運航空公司(后更名為MY CARGO),成為中國民航“走出去”的里程碑;斥資11.5億美元收購世界第四大集裝箱租賃公司GE SEACO(后更名為SEACO)100%股權(quán),成為當(dāng)年全球最大并購案之一。
然而,近年來,受世界經(jīng)濟(jì)持續(xù)低迷以及歐美主權(quán)債務(wù)危機(jī)影響,海航的部分產(chǎn)業(yè)也確實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如旗下的物流產(chǎn)業(yè),代表是海航物流旗下的航運業(yè)務(wù)虧損。
陳峰告訴《英才》記者:“航運業(yè)虧損之前,其實集團(tuán)已經(jīng)預(yù)警,但下面子公司還是動手晚了。海運業(yè)的情況,業(yè)內(nèi)其他公司都沒有預(yù)見到,我們也難獨善其身。物流業(yè)我還會重新打造。”
“要先把菜買進(jìn)來,然后再撿爛菜葉,把壞葉去掉”。按照陳峰的說法,為了應(yīng)對全球經(jīng)濟(jì)危機(jī),海航進(jìn)行了其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關(guān)停并轉(zhuǎn)”,自2011年7月至今,重拳之下的海航已累積關(guān)停并轉(zhuǎn)企業(yè)超過230家。以往確立的八大產(chǎn)業(yè)板塊也在2012年8月被再優(yōu)化為航空、實業(yè)、資本、旅業(yè)、物流等五大板塊,海航還撤消了華南、華北、東北等眾多區(qū)域總部和平臺公司,以遏制投資沖動。
李先華在總結(jié)此次調(diào)整時告訴《英才》記者:“林子一大什么鳥都有,原來海航集團(tuán)盤子小,項目都是核心骨干人員直接操盤,那個時代的管理者,是精挑細(xì)選,細(xì)心打理,我們做一個項目就成一個項目,后來產(chǎn)業(yè)、集團(tuán)太大了,我們把權(quán)力適當(dāng)下放了一下,導(dǎo)致有的干部責(zé)任心不強,自然出現(xiàn)了一些管控不到位的情況,但好在這些項目都是很小的項目。所以,我們用一年半的時間進(jìn)行清理,保持海航健康的機(jī)體。”
陳峰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做強核心企業(yè),打造核心產(chǎn)品,全面提升核心競爭能力。海航的核心主業(yè)由八變六,再由六變五,但是板塊的改變并不能在短期內(nèi)實質(zhì)性地改變原先八大板塊的業(yè)務(wù)種類數(shù)量,如海航實業(yè)涉及房地產(chǎn)開發(fā)、零售百貨、機(jī)場運營、金融投資四大領(lǐng)域,本身就是多元化公司。業(yè)務(wù)架構(gòu)方面,海航實業(yè)和海航資本在金融領(lǐng)域也有部分定位重疊。
在談及海航發(fā)展重心時,陳峰和李先華先后接受《英才》記者采訪都表示海航的根基依然是實業(yè),海航金融產(chǎn)業(yè)只是水到渠成的發(fā)展需要。對于海航來說,擁有銀行、保險、投資銀行、租賃、信托、證券、期貨、基金全金融牌照,海航的資本板塊猶如一個人的經(jīng)脈,遍布海航所有實業(yè),通過血液的流動,來為整個海航軀體提供能量。
對于海航的金融板塊,李先華曾提到:“海航要做以租賃業(yè)為核心的金融產(chǎn)業(yè)。因為租賃業(yè)剛剛起步,今后產(chǎn)值可以做到幾千個億。而其他的金融產(chǎn)業(yè),比如銀行、保險格局已定,證券業(yè)又過于分散。所以,海航以租賃業(yè)為紐帶、平臺。”
“海航發(fā)展租賃業(yè)務(wù),是在中國租賃業(yè)最低谷的時候開始的。海航從產(chǎn)融結(jié)合的戰(zhàn)略性方面考量,以融資租賃為起點介入金融,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海航資本執(zhí)行董事長劉小勇說,“一個企業(yè)在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發(fā)展壯大以后,必然會把產(chǎn)業(yè)經(jīng)營的手段和金融工具、金融手段相融合,比如GE。”
對于海航的管理層來說,運用資本市場調(diào)整融資結(jié)構(gòu),運用負(fù)債實現(xiàn)企業(yè)跨越式發(fā)展需要具有極高超的能力、智慧。
陳峰并不在意別人對于海航的褒貶,“海航如果欠一筆錢,有一筆逾期,銀監(jiān)會系統(tǒng)馬上就給你‘褒獎’了,所以你根本無法做到今天。”陳峰很自信。
密集的海外并購
四大航空公司中,2012年海航、東航分別實現(xiàn)凈利潤19.28億元、34.3億元,同比下滑26.7%、29.8%;國航、南航分別實現(xiàn)盈利49.5億元、26.3億元,同比下滑33.8%、48.22%。
“這是一個多么好的時代,但是我們的機(jī)會有限”,雖然海航凈利潤下滑最少,但陳峰依然無法釋然。海航雖已經(jīng)成為國內(nèi)第四大航空公司,但是“國內(nèi)根本不公平,好碼頭都被人占了。北京一個時刻就值多少錢。人家全占完了,北上廣這仨地,人家的航線比我們的好。”
“在國內(nèi),新疆、內(nèi)蒙全是我的,兔子不拉屎的地方都是我們?nèi)ァ鴥?nèi)支線的半壁江山,都在我們手里。”陳峰感慨頗多。
為了獲得更高的利潤率,海航在國內(nèi)攜手地方政府,發(fā)力支線航空的同時,從金融危機(jī)之始,就把目光轉(zhuǎn)移到了國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jī)爆發(fā)以來,海外股市大幅度縮水,資產(chǎn)價格大幅下降,這讓陳峰看到了國外并購的機(jī)會。“國外的基金兩三年就要退,因為要還人家錢,沒辦法,只好甩賣。”陳峰說。
2010年并購澳大利亞AllCO集團(tuán)航空租賃業(yè)務(wù)(現(xiàn)更名為香港航空租賃有限責(zé)任公司),收購?fù)炼滹w機(jī)維修公司MYTECHNIC、收購挪威上市公司GTB。
2011年收購新加坡GE Seaco集裝箱租賃公司、收購香港康泰旅行社。
2012年收購法國藍(lán)鷹航空48%的股權(quán)、投資非洲加納AWA航空公司。
2013年收購西班牙NH酒店集團(tuán)20%的股權(quán),與現(xiàn)有海航酒店合并后規(guī)模有望排名全國第一。
在航空產(chǎn)業(yè)海外布局上,陳峰著重歐洲和非洲兩個市場。“目前海南航空是中俄市場上運營航線數(shù)量最多的承運人,也是中方唯一運營非洲航線的承運人。非洲跟中國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日益緊密,我們希望以后開通直航,不要老轉(zhuǎn)來轉(zhuǎn)去。投資法國的航空企業(yè),可由此獲得國際航權(quán),并與國內(nèi)航線市場更好地銜接。”陳峰希望借助收購帶動國際航線,因為國際航線才是航空業(yè)利潤最大的業(yè)務(wù)。
截至2012年底,海航在境外實體運營企業(yè)28家,境外資產(chǎn)逾750億元,占集團(tuán)總資產(chǎn)的21%。
對于海外并購,陳峰認(rèn)為從資金上控股是一方面,關(guān)鍵是能否整合。“第一,并購的資源能不能與你現(xiàn)有的產(chǎn)業(yè)構(gòu)成整合能力;第二,它的文化和你能不能交融;第三,你是不是能夠把他的管理模式format(格式化)。當(dāng)然,你控股,自然具備上述條件,不控股,符合以上條件才能做。而核心是你的文化。”
海航并購法國藍(lán)鷹,是中國航空公司第一次走出去,把航權(quán)拿到。為此,陳峰還特意囑咐制作了法文版的海航員工十條。“我做完報告之后,群情振奮,法國員工集體背誦法文版的海航員工十條。”陳峰的企業(yè)文化演講頗具煽動性。
海航的海外并購不僅獲得了“外勢”,也獲得了“實地”,切實賺了錢。“我們購買的澳大利亞AllCO公司航空租賃業(yè)務(wù),已將優(yōu)質(zhì)資產(chǎn)順利裝入了國內(nèi)目前唯一的租賃上市公司渤海租賃。我們2011年用10.5億美元投資的GE SEACO集裝箱租賃公司,去年底收入就有3.7億美元、利潤1.8億美元。”陳峰說。
對于海外并購的資金獲得方式,陳峰告訴《英才》記者,因為并購的企業(yè)資質(zhì)非常好,70%的錢都來自于海外融資,海航只拿30%就可以。
“你比較喜歡行走江湖的感覺?”在采訪臨近結(jié)束時,記者問道。
“本來就是江湖人。”陳峰說。
江湖行走,世事難料。20年前的一架飛機(jī),將海航這間地方“鋪子”帶進(jìn)了世界大舞臺。作為一家民營企業(yè),海航闖蕩的道路并不平坦。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路上摸爬滾打成了中國民營企業(yè)家自信的來源,陳峰亦不例外。從給華爾街講故事開始,時代的造化和順勢而為的眼力,寫出了一篇武俠的“喻言”:彼時初入江湖,籍籍無名;此時談笑風(fēng)生,不畏浮云。
海航的發(fā)家史——差點兒胎死腹中
幾年前,陳峰曾行走于名山大川之間,不免遇到一些武林門派,雖然只是切磋,陳峰喜歡那種感覺。相對而言,商場上的拼殺,則更多的是生死。誰能想到正是20年前的那場生死之戰(zhàn)才有了今天的海航,又有誰知道,被人稱為“陳瘋子”的陳峰和他的一干兄弟,曾經(jīng)是那么的無助。
下海創(chuàng)業(yè),是那一代人的夢想,陳峰和他的兄弟們當(dāng)年放棄了國家機(jī)關(guān)的鐵飯碗。
“哪一年家里可以裝一部電話,哪一年局里能夠給我派車,我都能算得出來,當(dāng)一個人把自己的未來看得特別清楚的時候,就覺得特沒勁。”李先華回憶起當(dāng)年的往事,仍頗有感慨,“機(jī)關(guān)里很難實現(xiàn)人生價值,所以當(dāng)時我們這幫人就有想做一番事業(yè)的沖動。”
1989年,陳峰率先離開北京,來到海南。
采訪中,陳峰常常提到“機(jī)緣”二字,而當(dāng)初海航的成立,也是“機(jī)緣”巧合。一次偶然的機(jī)會,時任海南省省長的劉劍鋒找到陳峰,希望能夠借助陳峰多年的航空管理經(jīng)驗,幫助海南建立起自己的航空公司。
1990年,海南有600萬人口,沒有一家航空公司,而當(dāng)時的臺灣,2000多萬人口,有6家航空公司,差距雖大,但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市場需求巨大。
得到海南省政府的“批文”,陳峰發(fā)出了“英雄帖”,召集了在北京的“兄弟”,王健、李箐、陳文理等其他三位創(chuàng)業(yè)者先后加入。
當(dāng)時海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只有3個多億,發(fā)工資都很困難,需要中央補貼,拿出1000萬來辦航空,是很有魄力的。問題是,雖然省政府覺得很多了,但是對于辦航空公司來說,遠(yuǎn)遠(yuǎn)不夠,當(dāng)時購買一架波音737需要3億元。更不用說辦一家能夠和漢莎相媲美的航空公司。
資金尚未解決,同行的擠壓卻搶先一步。海南巨大的開發(fā)潛力和旅游資源,無疑讓所有航空公司都垂涎三尺,聽說海南要自己興辦航空公司的時候,一家大型航空公司感到了身邊的威脅。
“當(dāng)時他們看到我們這幫人還有點兒血性,日夜琢磨著把包機(jī)飛起來,勾畫著一個海南航空業(yè)美好的藍(lán)圖,就想到要把它扼殺在搖籃之中。如果我是那家航空公司的老總,我也會這么做。”李先華回憶說。
于是,這家公司開始游說海南省政府:一、要辦航空公司需要錢,可是省政府沒有錢;二、管理一旦出現(xiàn)問題,摔下來一架飛機(jī),說不好連領(lǐng)導(dǎo)的烏紗帽都會有問題。然后,這家航空公司提出,與其省政府自己辦,不如由這家航空公司在海南成立分公司,給海南調(diào)配十幾架飛機(jī),把航線開起來。
這家航空公司的游說,最終打動了海南省政府,雙方簽訂了合作協(xié)議。但是公開之前,并沒有告知還在一心創(chuàng)辦海航的陳峰等人。
事后,陳峰得知,協(xié)議里對陳峰等一干人馬,約定是“量才錄用”。但是對手的傲慢卻給了陳峰等人一次翻盤的機(jī)會。
“他們以為一槍把我們都打死了,哪知道我們躺了一會兒,擦干身上的血跡又重新站起來了。從那時候起,海航就開始出現(xiàn)在中國的民航江湖。”創(chuàng)業(yè)者之一的李先華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如此調(diào)侃。
起于草莽,創(chuàng)立之初就充滿波折,這讓海航創(chuàng)業(yè)者從伊始就具有危機(jī)意識,而這或許也塑造了海航不斷擴(kuò)張的基因。“我們深知中國國情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用中國文化的智慧,抓住發(fā)展的每一次機(jī)會。”陳峰如此總結(jié)海航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
獨家高端領(lǐng)袖對話 爭斗中交融
《英才》:你在上世紀(jì)90年代初就見到索羅斯了么?
陳峰:索羅斯是后來才見到的,開始是索羅斯的助理。
《英才》:當(dāng)時是怎么促成合作的?
陳峰:海航的運營逐漸成功之后,進(jìn)了幾架飛機(jī),導(dǎo)致負(fù)債率太高了。于是有人告訴我上美國可以發(fā)股票。于是我和我們的副董事長——當(dāng)時我們倆還年輕,不到40歲——提著包到華爾街去了。那時候我對美國華爾街的投行一無所知,真不懂。但是不懂也得裝懂,夾個包就跟人家談。我們倆英文都很好,我英文都是自學(xué)的,一天課都沒上過,Very Easy。到那一看是講故事,講故事我是內(nèi)行啊,于是就給他們講海航用1000萬起步。
索羅斯下面也有航空集團(tuán),也做投行業(yè)務(wù)。后來他的投資總裁聽到我的發(fā)言和回答問題。他說你有這么精彩的故事,而且企業(yè)家本人又在這兒。
后來他問我企業(yè)在什么地方。我找出地圖來,一看壞了,英文地圖啊,海南只有那么一點,沒有文字,就SOUTHOFCHINA SEA這幾個字。
于是,我說你看見越南了沒有?越戰(zhàn)美國人都沒有打贏,你知道什么原因嗎?是你們怕死。中國人不怕死,光腳不怕穿鞋的。大家哄堂大笑,我又告訴他們從越南坐船幾個小時就到我們這兒。他一看我這么幽默,干脆就買你25%的股份了,沒隔三個星期把錢匯來了,我做了一堆股票給他們。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航空公司就這樣產(chǎn)生了。
海航式地產(chǎn)模式
《英才》:大家覺得海航在地產(chǎn)方面更多的是資本運作,而不像是傳統(tǒng)開發(fā)商的產(chǎn)業(yè)運作模式,你認(rèn)同么?
陳峰:這個事情外界不是很了解。首先我們不是那種典型的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出身,實際上我們做地產(chǎn),是在企業(yè)發(fā)展過程中拉大產(chǎn)業(yè)鏈條帶來的這個產(chǎn)業(yè)。海航的產(chǎn)業(yè)鏈有我們自己的特色,主要圍繞著航空干,比如臨空產(chǎn)業(yè)園區(qū),另外加上“中國集”,和我們特色的這種跟業(yè)務(wù)相關(guān)的地產(chǎn)做的,其他的都很少。
《英才》:你覺得傳統(tǒng)房地產(chǎn)現(xiàn)在的問題在哪兒?
陳峰:我們不能走房地產(chǎn)開發(fā)商的老路。中國的房地產(chǎn)出的問題是過去太“暴利”,為什么這么說?本來應(yīng)該用3.0的鋼筋,他給你用2.0。水泥中間偷工減料,比比皆是,他們黑錢掙的太多了。有時候“機(jī)緣”就是這樣的,這次調(diào)控給你往死里整,讓他們把掙的錢趕緊吐出來。你不能買塊地,畫個圖紙,賣樓花就把錢全掙了。在國外房地產(chǎn)有這么高的回報率嗎?根本不可能有,國外的回報率有20%那都相當(dāng)不得了,而咱們都可能到200%。
“勢”的哲學(xué)
《英才》:你怎么看中國未來的發(fā)展?
陳峰:一次一位朋友請我去給一些企業(yè)家講課,在上海的一個會議中心,3000多人。一看那么多人,我說給你們傳達(dá)一下十八大報告吧。
《英才》:為什么?
陳峰:一個人最大的能耐就是運用勢,形勢的勢。
中華民族百年復(fù)興的夢想,只靠一代人怎能完成呢?這個民族總沒斷這個夢想。今天這個世界發(fā)生的問題都是勢。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生命本身,長期積累的問題到時候就會質(zhì)變。
正所謂“大勢至菩薩一到,眾神退位”,沒辦法。所以人最大的能力,是運用勢。而黨的政策是最大的勢,你這個不能信服怎么行呢?十八大就是講未來中國五年的大走勢。
《英才》:隨著海航不斷擴(kuò)張,和被并購方合作不愉快怎么辦?
陳峰:斗爭不一定不愉快。“團(tuán)結(jié)-斗爭-團(tuán)結(jié)”,咱們可以互相交融,在發(fā)展中大家都可以規(guī)范起來。
《英才》:你不斷重組的過程也是在不斷斗爭?
陳峰:從來就是處于矛盾之中,只要有兩個人的地方都是。從來都是為了合作,斗爭也是為了合作,為了公司搞好,為了廣大股民的利益。
怨天尤人沒有用
《英才》:和10年或者20年前相比,你覺得民營企業(yè)的生存環(huán)境有怎樣的變化?
陳峰:既好又不好。好在哪兒呢?從海航成功發(fā)展的角度來說,不能說不好,這10年我們造就了一個世界級企業(yè)。
所謂環(huán)境也有不好的那一面,金融危機(jī)導(dǎo)致全球發(fā)生變化,再加上中國國內(nèi)的轉(zhuǎn)型期,人們這種貪欲和浮躁構(gòu)成全社會的一些問題。這個貪欲和浮躁是隨著財富的增長不斷變大,而不是變小。
當(dāng)前這種浮躁的環(huán)境,并不只是光影響企業(yè)和社會,政府也受影響。矛盾突出,就構(gòu)成了一種人們的不平衡和怨恨。
咱公平來講,這10年人們的生活有很大的變化。就是社會最低層的人,生活也有很大變化。但為什么還那么多矛盾,怨氣呢?天下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心理不平衡。
《英才》:你覺得應(yīng)該如何解決?
陳峰:在這個情況下,我認(rèn)為在發(fā)展物質(zhì)文明同時,要在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修養(yǎng)上帶來巨大的提升。
這是要靠全體人民,全社會,在黨和政府的領(lǐng)導(dǎo)下,逐步用一種加強社會法制建設(shè)和文化建設(shè)的辦法,來渡過這個痛苦的時期。怨天尤人沒有用。
一個成熟的企業(yè)家、政治家應(yīng)該站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遠(yuǎn)的、根本利益上的角度,然后不斷調(diào)整、改革,通過文化的熏陶,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個慢功夫,有時候會需要一代人。
責(zé)編:admin
免責(zé)聲明:
凡本站及其子站注明“國際空港信息網(wǎng)”的稿件,其版權(quán)屬于國際空港信息網(wǎng)及其子站所有。其他媒體、網(wǎng)站或個人轉(zhuǎn)載使用時必須注明:“文章來源:國際空港信息網(wǎng)”。其他均轉(zhuǎn)載、編譯或摘編自其它媒體,轉(zhuǎn)載、編譯或摘編的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對其真實性負(fù)責(zé)。其他媒體、網(wǎng)站或個人轉(zhuǎn)載使用時必須保留本站注明的文章來源。文章內(nèi)容僅供參考,新聞糾錯 airportsnews@126.com